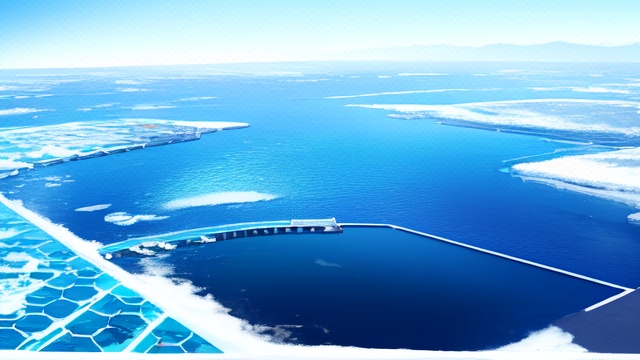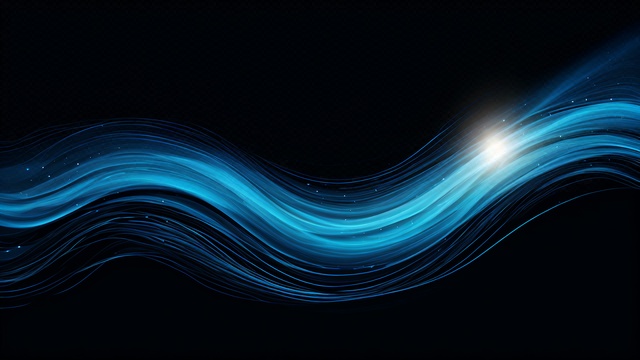西装定制南康-西装定制厂
[词的履历]履历用什么词形容

口袋 某天,我扯着母亲的衣角,用一种类似小帝王的口气说:“给我买套西装。”大概八岁吧,身体如笋,和萧索的篱笆竞赛身高,刚好能趴在窗口,打量世界。母亲犹豫了半晌,从抽屉里翻出卷尺,给我量了尺寸,到村东的裁缝店定制了一件。几天后,我跟着母亲去取西服,结果发现,竟然没有一个口袋。我扔了它,咬着牙,恨恨地跺上几脚。
这件事像燃点很低的磷,与内心扑腾的渴望轻微擦碰,火花四起。
我对口袋的钟情与信任感源自它与肌肤的贴近、对外界守口如瓶的品性及安之若素的机警。很多年,在服装店左右挑选的标准并非款式,而是口袋的样貌及深度。我将其看成我的第二个财产储蓄所,渐渐的,它在我的内心筑起了排斥使用钱包的高墙。
从口袋里的事物可以描出时间的线索。十四岁之前,我生活在泥土之上。当时有种隐秘的偏好,无所事事地走在村子里的时候,一只手在兜里掏出某件物什,细细把玩一会儿,再放回口袋。无非是铮亮的弹珠、胶球、象棋子、蚕盒或碎瓷板,几颗闪亮的弹珠足以成为我在伙伴中炫耀的资本。偶尔也到河边翻找一些小石子、斑斓的贝壳,填充着空落的口袋。身体拔节,似乎一夜间将口袋里这些小东西掏空。我丢掉的其实是一些不复苏醒的童趣。
十四岁,我去南康县城读高中,钥匙便在这时走进口袋,这意味着,从那时起我必须独自掌管某扇门的开闭。两年后,口袋里出现了新东西:傻瓜相机。镜头下,我喜欢上了古典建筑,常常对着一幢即将坍圮的老房子出神——飞起的檐角,褪色的门楣,精雕的窗棂,发霉的青砖,粗壮的椽梁……我用镜头和笔疯狂地爱着它们,一个少年,爱着一切过时的事物。
而现在,把口袋翻出来,只有工行卡、联想手机、身份证、硬币……我们重复确认着身体之外的胃装置是否饱满。这些物件,是否可以证明它的饱满?
黄泥房
厨房南面的水井上,瓷片镶嵌的年份数字被沙埋着,拨开看,上世纪的字仍水水地醒着。我没有经历一九八七这个年份,关于黄泥房的建造史,也没有文字与图像注释。当年我的祖辈们如何将软软的黄泥扶成近十米的高墙;又是如何将瓦砾在椽子上铺叠成一个盛大而狂欢的排比句,梳理着江南绵绵无尽的雨水……我都不从得知。我只知道,作为村里有威望的私塾先生的祖父,深爱着他那一椽一檩亲自建造的黄泥房,他不止一次提到,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。他不愿住进儿女建造的砖房,二〇〇二年春末的那次大洪水,黄泥房沦为危房,他才终于答应搬进新房。半月后,洪水退去,他又迁回黄泥房中。
二〇〇六年深冬的某个下午,祖父一跤摔成了脑溢血,随后在老宅大厅的硬门板上痛苦地躺着。冰冷的手握着我,一些话被哽在喉间。三天后,他最后环视了房子一周,满足地睡进了黄泥房侧棚的棺椁里。过去,我从来不敢靠近那个朱红的长条形木箱,认为那是鬼魂藏匿的地方。很早以前,我的母亲就在那里围了一圈篱笆,养着些家禽。
许多夏夜,我坐在黄泥房里写字,写不了一会儿便停下来,眼睛瞄着墙上的年画、挂历、旧奖状、睡眠的钟,上世纪的味道和景象就窜了出来,遥远的人和事排着队与现在的我握手。顶上是从房梁的板缝间偷逃出的稻穗和枯豆条,还有一把蛛网劫持的陈年吊扇。长长的木梯斜搭在阁楼上,上面是旧物仓库,那时候祖母身体还很硬朗,经常把一些需贮存的咸菜、米果、月亮粑等搬上去,用蛇皮袋层层包好,堆到米缸里。那里还有坏电扇、旧玩具、雨伞、陶器、木箱里的课本……还有,水车。十多年前,在赣南,每家都有。而我现在的叙述已找不到参照物,只凭记忆再现。我一直以为水车孤独而悲戚地蜷缩在黄泥房的阁楼上,在黑暗中呼吸,是为时代而黯然伤神。有一天,我顺着木梯爬上阁楼,发现原来存放水车的位置,只遗留着几条虚痕。我下楼问祖母水车哪儿去了,她说反正也用不上,又占位置,我劈碎后当柴烧了。在一个患有严重恋旧癖的写作者眼里,这样的回答如同是,我把你的手稿烧了。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卡莱尔的在手稿焚灭后奋笔再书的钢铁意志。那些沾染着时光霉味的旧物,有着与人相近的生命体征,沉稳的脉搏、匀细的呼吸,以及绝望的叹息。它们在长年累月的劳作后,并没有收获应得的尊重。许多陈年旧物在二〇〇〇年以后的光阴漩涡中悄悄消失了,它们如同多年以前我尝过的一种姜饼的味道,我无法向你描述,比如晒米的木质风车、独轮车、石磨、煤油灯、缝纫机等,和苍老的祖父一样,它们隐匿于黄泥房的暗处,然后归于记忆的虚无。
多年前,祖父的房间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。祖父上圩未归,我便着迷地在他房间里搜寻着铜板、大洋之类的古玩。他是位自学成才的眼疾医生,抽屉和橱柜里有《本草纲目》之类的医书。那些年,时常有一些都市来的眼疾患者,提着大包礼品,在寻觅千百度后敲响我祖父的房门。很久以来,我都感到困惑,几乎一辈子没出过小镇的祖父,他的医术名声是如何传播的。在眼疾者满意地离去之后,祖父便把我叫到跟前,摸着我的脑袋,塞给我一把糖果,说:“拿去吃吧。”我略微尝出了祖父颔首间的喜悦,但直到许多年后,我开始学习写作,才真正恍然当时他那种如同完成了一件作品般的快感。
黄泥房地面上黑硬的土在梅雨时节常常散发出一股霉豆腐的味道,我从五万多个清晨醒来,从柚子花和这种泥土糅合的味道中醒来,推开大门,在石凳上坐下来,揉着眼,看见十米外的柚树上落着一只花斑鸟,一直静止在枝丫上。这只鸟了吗?还是在睡觉?我走上前,花斑鸟变成了一只红色的塑料袋。多年之后,叔辈已将黄泥房拆除,我遥想着一九八七年祖辈们建造它时的情景……我已经无力复述,那些我不曾亲见的往事,只有花斑鸟飞进了我的记忆,在日后的一些年里,它既是我在纸上生活时惯于采用的技巧,也是如今我在废墟上通过遐思回到黄泥房里的唯一方式。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